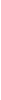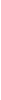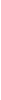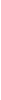宋慈洗冤笔记4(出书版) - 第5节
宋慈听完这番讲述,想到母亲收下了平安符,却在当天遇害离世,世事实在是无常难料,倘若真有神佛庇佑,那该有多好。他呆了片刻,忽然问道:“古公公现在何处?还在御药院吗?”
“古公公早已不在人世了。”韩絮摇了摇头,“圣上登基后,古公公升为都都知,没几年便去世了。”
都都知负责掌管整个入内内侍省,算是大宋宦官的最高官职,这位古公公从御药院的奉御,一跃成为宦官之首,倒是令宋慈多少有些诧异。他又问道:“没几年是几年?”
“记不太清了,三四年吧。”
赵扩登基是在十一年前,如此算来,古公公离世已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宋慈没再说话,想着方才韩絮所述之事,渐渐入了神。韩絮饮尽盏中之酒,抬头望着夜空,只见那几缕暗云升起,慢慢地笼住了月亮。
如此过了好长时间,宋慈才开口道:“时候不早了,明日还要行课,该回去了。”看向韩絮,“郡主独自居住在外,还是当有一二仆从,跟随照看为好。”
韩絮知道宋慈是在担心她的安危,道:“劳宋公子挂心,多谢了。”她过去几年在外行走,是一直带了仆从的,但此次重回临安,是为了查访禹秋兰的死,她不想让太多外人知道此事,这才把所有仆从遣散回家,独自一人住进了锦绣客舍。
宋慈不再多言。他回头望去,刘克庄和辛铁柱的身前已堆满了酒瓶和酒坛,两人喝得大醉,兀自长言兵事,大论北伐。宋慈深知北伐之艰险难为,并不赞同此时北伐,刘克庄虽也明白这些道理,但其内心深处却是支持尽早北伐的,总盼着早些收复故土。他二人互为知己,明白对方想法上的不同,因此少有谈及北伐。难得遇到辛铁柱这么大力赞同北伐之人,刘克庄一说起这话题来,那真是辩口利辞,滔滔不竭,周围不少酒客被吸引得停杯投箸,每每听他谈论到精彩之处,都忍不住击掌叫好。
第三章 客舍旧案
刘克庄一觉醒来,已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到习是斋的,只记得昨晚自己在琼楼高谈阔论,说到兴奋之处,想跳上桌子,却一个没站稳,摔了下来,后面的事便记不得了。他望了一眼宋慈——宋慈已穿戴整齐,坐在长桌前,就着一碗米粥,吃着太学馒头——料想昨晚自己不是被宋慈扶回来的,便是被宋慈背回来的。他坐起身子,只觉额头生疼,伸手一摸,能感觉肿起不少,可见昨晚那一跤着实摔得不轻。想到琼楼聚集了那么多酒客,自己只怕是当众出尽了洋相,宋慈带自己离开时定然很是尴尬,他忍不住哈哈一笑。
“你再不起来,早饭可吃不及了。”宋慈另盛了一碗米粥,搁在长桌上,拍了拍身下的长凳。
为了迎接皇帝视学,太学行课推迟到了上元节后。今日是正月十六,乃是新一年里第一天行课,迟到可不大好。刘克庄飞快地穿衣戴巾,被褥随意一卷,坐到了宋慈的身边。大口吃粥的同时,刘克庄不忘问昨晚花了多少酒钱。他知道宋慈手头没他那么宽裕,加之昨晚的酒大部分是他和辛铁柱喝掉的,所以打算把钱补还给宋慈。宋慈却说昨晚不是他付的钱,是韩絮结的账。刘克庄往嘴里塞了一大口馒头,整张脸圆鼓鼓的,含糊不清地笑道:“原来是郡主请的客,甚好,甚好!”
刘克庄快速吃罢早饭,便与宋慈同去学堂上课。
太学的课程分为经义和策论,还可兼修诗赋和律学,隔三岔五还要习射。授课通常是分斋进行,不同的斋舍,授课内容也不相同,一些斋舍侧重经义,授课内容多为经史子集,会选择心性疏通、胸有器局、可任大事的学子入读,另有一些斋舍侧重治事,授课内容更偏重实务,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等等。虽是分斋授课,每斋只容三十人,但太学行课允许旁听,无论是其他斋舍的学子,还是外来之人,都可入内听课,尤其是一些知名学官授课之时,听课之人往往远超其额,比如胡瑗,在其任太学博士讲《周易》之时,常有外来请听者,多至千数人,再如孙复任国子监时,在太学里开讲《春秋》,来听课的人莫知其数,堂内容纳不下,许多人都是挤在堂外旁听。
如今太学里的学官,讲课最为吸引人的,就数真德秀和欧阳严语。这二位太学博士都是讲授经义的,习是斋是偏经义的斋舍,今日上午和下午,正好各有一堂这二人的课。
上午是真德秀的课,宋慈虽然心中装着案情,却还能克定心力,如往常一般认真行课,可是到了下午欧阳严语授课时,宋慈却怎么也集中不了心神。经过了昨天那一番追查,母亲的旧案便如那笼住月亮的暗云,一直遮罩在他的心头。他一看见欧阳严语,思绪便忍不住回溯,想起母亲遇害那天,自己随父亲前去琼楼赴宴的事。
那日禹秋兰一大早去玲珑绸缎庄后,宋巩在客房里教宋慈读书,一直教习至午时,才关好门窗,带着宋慈前去琼楼赴宴。这场酒宴由欧阳严语做东,不只请了宋巩,还请了太学里的几位学官,那几位学官都曾求学于蓝田书院。各人源出同一书院,相谈甚欢,席间喝了不少酒。宋慈记得母亲的叮嘱,贴在宋巩耳边说起了悄悄话,让父亲少喝些酒。可席间各人说起蓝田书院的故人旧事,又大谈理学,再预祝宋巩金榜题名,一盏又一盏的酒敬过来,宋巩只能一一饮下。殿试之后,说不定他也会被选入太学出任学官,所以他明白欧阳严语请来这几位学官,是为了让他提前结交这些人,将来当真入太学任了职,也好多些人帮衬照应。
这一场酒宴持续了很久,直到未时仍没结束。宋巩不想辜负欧阳严语的一番好意,一直没有提前离开。到了未时过半,他却忽然起身,说有事出去一下,请欧阳严语照看宋慈片刻,又叮嘱宋慈道:“你留在这里别乱跑,好好听欧阳伯伯的话,稍微等一会儿,爹去去便回。”他也不说去做什么,起身快步下楼去了。
说是去去便回,可宋巩这一去,过了好长时间,一直到席间各人吃喝尽兴、酒宴行将结束之时,他才回来。他脸色有些发红,额头微微冒汗,似乎这一去一回走得很急。也正是在未时,禹秋兰被韩淑和韩絮送回了锦绣客舍,后来死在了行香子房中,而宋巩这一去一回,让他背上了杀妻之嫌。府衙司理参军带着一群差役前来查案,怀疑宋巩离开琼楼,是回到了锦绣客舍,杀害禹秋兰后,又赶回了琼楼。琼楼与锦绣客舍相距不算太远,宋巩离开那么长时间,往返一趟杀个人,那是绰绰有余。
对于自己的突然离开,宋巩说是在琼楼饮宴之时,透过窗户看见韩带着几个仆从,跟随一抬轿子,从楼下大街上招摇而过。他想起宋慈被韩欺负一事,想讨要一番说法,这才起身下楼。
宋巩走出琼楼时,韩已走远了一段距离。他快步追去,一直追过了新庄桥,又拐了一个弯,才拦下了韩一行人。宋巩说起百戏棚的事,韩却拒不承认,叫几个随从把宋巩轰走。争执之际,那抬轿子起了帘,韩的养母吴氏露了面。
原来这天一早,吴氏带着韩出城游玩。阳春三月,正是观赏桃花的好时节,城北出余杭门,过了浙西运河,沿岸有一片桃林,时下桃花盛开,比之西湖拂柳又是另外一番景致。加之这一日天气晴朗,还有微风吹拂,最适合游玩赏花,母子二人在城外玩得兴起,一直到未时才回城。韩在外人面前顽劣霸道,在吴氏面前却一贯装出乖巧懂事的样子,想方设法讨吴氏的欢心,比如这次出行,吴氏让他一起乘坐轿子,他却说自己长大了,身子长重了,怕轿夫抬着太累,宁愿下轿步行,还说自己年少,正该多走些路。吴氏对此很是满意,在她眼中,韩这个养子,那是万里挑一的好儿子。
吴氏问清楚宋巩为何拦住韩,又向韩询问实情。韩却说根本不认识宋巩,也没见过什么宋慈,说他前些天是去百戏棚看过幻术,但没与任何人发生过冲突。宋巩记得那个右手伤残的虫达,说要找此人做证,可虫达并不在这次出游的几个仆从当中。韩一口咬定没欺负过任何人,说是宋巩认错了人,还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说到急切之处,竟委屈得哭了起来。吴氏见状,对韩所言深信不疑,以为宋巩是想敲诈钱财,便吩咐随从将宋巩轰走。韩心里极其得意,见几个仆从对宋巩动粗,趁着背对吴氏之时,还故意冲宋巩狡黠一笑。
宋巩辩不得事理,讨不得公道,想到宋慈还在琼楼,只好先回去。他尽可能不在宋慈面前表露出愤懑和沮丧,带着宋慈返回了锦绣客舍。他到柜台取房门钥匙,吴伙计说禹秋兰已经回来了,钥匙早已给了禹秋兰。他回到行香子房,一推开虚掩的房门,就看见阳光透过半开的窗户,照得桌上地上全是一格格的光影,而在这一格格的光影之间,是一摊触目惊心的血迹。而禹秋兰正倒在床上,双腿掉出床沿,陈旧泛白的粗布裙袄已被鲜血浸透。宋巩大惊失色,向禹秋兰扑了过去。宋慈紧随父亲走进房间,目睹母亲惨死的一幕,小小的身子定在原地,浑身止不住地发抖。接下来吴伙计赶去府衙报案,司理参军带着仵作和一众差役赶到现场。一番查问之后,司理参军找来欧阳严语,问明宋巩酒宴期间离开一事,也不听宋巩辩白,便将宋巩当作嫌凶,抓去府衙,关入了司理狱。
随后的那段日子,漫长得好似度日如年。宋慈被欧阳严语接回了位于兴庆坊的家中照看,每每问起父亲如何,欧阳严语知他年幼,怕他担心,都只说些宽慰话,涉及案情的任何事,始终不对他提起。如此持续了十多天,宋巩才洗刷冤屈,得以出狱。出狱之后,殿试已过,宋巩因为凶嫌入狱,断送了大好前程。他不等府衙查清真相、抓住凶手,便扶着妻子灵柩,携着宋慈返回了家乡建阳。此后十五年间,他潜心钻研刑狱之事,做仵作,任推官,但始终绝口不提亡妻一案,也不让宋慈有机会接触此案,就连宋慈来临安太学求学,他也是多次反对,最终不得已才点头同意。
回忆着这些往事,再看如今的欧阳严语,其人鬓发斑白,皱纹深刻,已然苍老了太多太多。宋慈进入太学快一年了,已不知见过欧阳严语多少次,欧阳严语也知道他是谁,但两人都不愿再提起当年的事,因此彼此间一直只以师生相处。宋慈不想任何人知道他的过去,唯独对刘克庄提起过这起旧案。他从未忘记母亲之死,不然也不会从小钻研刑狱之事,但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太学生,无权无势,根本不可能翻查旧案。他原本是想早日为官,朝提刑官的方向努力,只盼有朝一日能获得实权,重查这起旧案。但他没想到自己会卷入何太骥一案,又得韩絮举荐成为提刑干办,一连串的凶案查下来,竟获得了虫达一案的查办之权。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在指引,指引他不断地接近母亲的案子。虫达极可能与他母亲之死有关,昨晚听完韩絮的讲述后,他凝望着暗云藏月的夜空,暗暗下定了决心,要在查清虫达之死的同时,一并追查他母亲的案子。
既已下定决心,那么首要之事,便是去城南义庄找到祁驼子,向当年府衙的这位仵作行人问清楚,查验他母亲的尸体时,究竟出了什么错。行课结束后,与刘克庄并肩返回斋舍的路上,宋慈准备把自己的这一决定告诉刘克庄。正当他要开口时,刘克庄先说话了:“好好的桃树,你们挖了做什么?”
刘克庄这话不是冲宋慈说的,而是冲道旁的几个斋仆说的。道旁种有几株不大不小的桃树,那几个斋仆正挥动锄头,将桃树一株株地挖出来。时下虽然天寒,但几个斋仆干的是力气活,个个都累得汗出如浆。
几个斋仆之中,有一人是因为岳祠案与宋慈打过交道的孙老头。他认得宋慈和刘克庄,锄头往地上一杵,抹了一把额头上密密的汗,应道:“是刘公子和宋公子啊。”又向挖出来的几株桃树指了一下,“祭酒大人吩咐把这几株桃树挖了,小老儿便来忙活了。”
刘克庄道:“开春在即,这几株桃树眼看离开花不远,挖了岂不可惜?”
孙老头朝那几株挖出来的桃树看了看,道:“刘公子说的是,挖了确实可惜,不过祭酒大人说了,桃花太艳,种在学堂不成体统,吩咐我们挖干净了,过些日子弄些松柏来,栽种在此。”
刘克庄只觉得不可理喻,转头向宋慈道:“这个汤祭酒,居然见不得桃花娇艳。花能有什么错?人心不正,见什么都不正,难道换了松柏,便能正直得起来?”说着无奈地摇摇头,“去年你我入学时,这几株桃树花开正好,足不出户便可赏春。桃花落尽无春思,偌大一个太学,就这里看着有几许春色。今年要看桃花,怕是得去城北郊外了。”
听刘克庄提起去城北郊外看桃花,宋慈不禁想起十五年前,母亲也曾有过这样的许诺,还说等他父亲殿试结束,便一起去城北浙西运河对岸,观赏那沿岸的桃花盛景,只可惜母亲后来遇害,这许诺就此成空,成为他一辈子的遗憾。后来母亲归葬家乡建阳,下葬之时,父亲带着他在母亲坟墓旁种下了一株桃树,此后每年桃花开放之时,他都会去坟前坐上一整天。去年三月间,他来临安求学之前,也是去母亲坟前,坐在桃树之下,陪了母亲一整天,随后才启程北行的。如今他身在太学,不能归家,母亲今年看来要孤单了。他想到这里,忽然道:“我今晚想去一趟城南义庄。”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令刘克庄为之一愣,随即问道:“你下定决心了?”
刘克庄深知宋慈素来行事,要么不做,要么便做到底。上次得知祁驼子与亡母一案有关后,宋慈并未立即去城南义庄找祁驼子,可见当时宋慈还没有决意追查此案,如今宋慈提出去城南义庄,那便意味着他已经准备好了,决心触碰此案,并追查到底。
宋慈看向刘克庄,目光极其坚定,用力地点了一下头。
此次去城南义庄,刘克庄照常叫上了辛铁柱,宋慈同样知会了韩絮。为了方便韩絮,一行人仍是雇车出行,在夜幕降临之时,来到了城南义庄。
城南义庄一如上次那般孤寂冷清,大门未锁,一推即开。
义庄内不似上次那样点着灯笼,一眼望去尽是昏黑,只能隐约看见一口口大小不等的棺材,或横或竖地搁了一地。忽然“啊呀”声起,几团黑影从窗户破洞中扑棱棱飞出,原来是几只准备夜栖的寒鸦。四人受此一惊,都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
“人不在?”一片死寂之中,刘克庄小声道。
祁驼子虽是义庄看守,平日里却是嗜赌如命,常去外城柜坊,守在义庄的时候不多。整个义庄无声无息,映入眼帘的只有棺材,不见半个人影,看来祁驼子又外出赌钱了。
宋慈想着去外城柜坊寻人,正打算回身,忽然角落里传来一阵细碎的“咯咯”声。这声音时断时续,听起来像是在轻轻敲击什么,又像是在磨牙。刘克庄横挪一步,有意无意地挡在了韩絮的身前;辛铁柱不为这阵声音所吸引,举目四顾,留意四下里有无危险;宋慈则是循声辨位,朝角落里慢慢走去。
角落里停放着一口狭小的棺材,这阵“咯咯”声正是来自于这口棺材之中。宋慈于棺材边停步,探头看去,棺材没有盖子,里面黑乎乎的,隐约可见一具尸体蜷缩于其中。忽然“咯咯”声大作,这具尸体一下子从棺材里坐了起来。
辛铁柱当即飞步抢上前,宋慈却把手一抬,示意辛铁柱停下。宋慈离得很近,此时已经看清,这具“尸体”后背弓弯着,其上顶着一个大驼子,正是此前有过一面之缘的祁驼子。祁驼子没有睁眼,嘴里“咯咯”声不断,那是牙齿叩击之声,也不知是被冻成了这样,还是做了噩梦被吓得如此。祁驼子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了片刻,忽然倒头下去,又躺回了棺材里。这般一起一倒,他竟还睡着,一直没醒。
刘克庄虽然挺身护着韩絮,实则他自己也被祁驼子这一出吓得不轻。等他看明白后,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从怀里摸出火折子,点亮了义庄里悬挂的白灯笼,随即走到棺材边,用力拍打起了棺材。
祁驼子被这阵拍打声所扰,独眼睁了开来。
“还记得我吧。”刘克庄望着祁驼子,脸上带着笑。
祁驼子慢慢坐起,无神的眼珠子动了动,看了看刘克庄和宋慈等人,像是没睡醒,又要朝棺材里躺去。
“你还欠我三百钱呢,说了会来找你拿钱,眼下可不是睡觉的时候。”刘克庄一把拉住祁驼子,不让他再躺倒。
“是我的,我的……”祁驼子胸前的衣服被拉住,双手忙朝胸前环抱,像是在护着什么东西。
刘克庄记得上次给了祁驼子五百钱,祁驼子就曾这般护在怀里,以为祁驼子怀里揣着钱,笑道:“看来你这几日手气不错,在柜坊赢了不少钱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可别抵赖。”
“没钱,我没钱……”祁驼子护得更紧了。
“你过去是临安府衙的仵作?”宋慈忽然开口了。
刘克庄并不在意那三百钱,只是故意为难一下祁驼子,听得宋慈问话,便放开了祁驼子。
祁驼子护在胸前的双手慢慢松开了,头仍然摇着:“什么仵作……记不得了……”
他吧唧着嘴,似乎口干舌燥,从棺材里爬出,揭开墙角一口罐子,拿起破瓢舀水来喝。
“‘芮草融醋掩伤,甘草调汁显伤’,你能说出此法,不可能记不得。”宋慈道,“你还有一个弟弟,唤作祁老二,住在城北泥溪村,以烧卖炭墼为生,我与他见过面,对你的过去已有所知。十五年前,锦绣客舍的案子,是你办的吧?”
“锦绣客舍”四字一入耳,祁驼子拿瓢的手忽然一顿。但他很快恢复正常,喝罢了水,把瓢扔进罐子,又要回棺材里躺下,根本没打算应宋慈的话。
宋慈继续道:“此案牵涉一家三口,妻子为人所害,丈夫蒙冤入狱,他们还有一孩子,当年只有五岁。”提及自己,微微一顿,“如今这孩子已经长大,欲为亡母直冤,特来这城南义庄,求见于你。”
祁驼子正要爬回棺材,闻听此言,乜眼来盯着宋慈,似乎明白了宋慈是谁。这么盯了几眼后,他把头偏开了,仍是一声不吭,但没再回到棺材之中,而是站在原地。
“寄顿尸体,一百钱;打听事情,两百钱。”刘克庄忽然伸手入怀,掏出几张行在会子,“两百钱未免太少了,我先免去你那三百钱欠债,再多给你三五百钱,就算多给你三五贯也行。”
祁驼子一向嗜赌爱钱,刘克庄又想使出“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一套,哪知祁驼子没理睬他,甚至没向他手中的行在会子瞧上一眼。他笑道:“你这老头,有些意思。这钱你当真不要?那我可收回来了。”
说着他作势要把行在会子揣回怀中,祁驼子仍是无动于衷。
“你是当年那个有些驼背的仵作?”韩絮忽然蹙眉上前,借着白惨惨的灯笼光,打量着祁驼子的身形样貌,“当年你去过嘉王府,却被王府护卫驱赶,我说得对吧?想不到你如今竟变成了这样。”
祁驼子不认得韩絮是谁,朝韩絮看了一眼,移开了目光,仍是不说话。
祁驼子没有再爬回棺材里睡觉,而是一直站在那里,这般长时间一动不动地不作声,足可见祁驼子应该是想起了什么,只是不愿开口而已。祁驼子因为锦绣客舍的案子丢掉了仵作之职,后来又连遭变故,家中失火,妻女身死,自己瞎了一目,从此性情大变。宋慈理解祁驼子为何不愿开口,不打算再勉强,见刘克庄又要问话,冲刘克庄轻轻摇了一下头,道:“我们走吧。”说完转身向义庄大门走去。
刘克庄也知晓祁驼子的过去,将那几张行在会子放在一旁的棺材上,随宋慈离开。韩絮和辛铁柱见状,也都转身而走。
“我记得那人,他名叫宋巩。”宋慈即将走出义庄时,祁驼子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他行凶杀妻,证据确凿,本就是杀人凶手。”
宋慈闻言一惊,回头望着祁驼子,声音发颤:“你说……什么?”
“你就是宋巩的儿子吧,当年我去锦绣客舍时,你还没这口棺材高。”祁驼子摸了摸身边的棺材,声音发冷,“我说你爹是凶手,就算他侥幸出了狱,杀人的也还是他。”
当年祁驼子随司理参军赶到锦绣客舍时,宋慈的确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但那时祁驼子的后背只是稍微有一些驼,眼睛也还没瞎,衣着很是干净,与如今可谓判若两人,是以宋慈上次来城南义庄见祁驼子时,根本认不出。他原以为祁驼子知晓一些独特的验尸之法,定然精于验尸,当年又负责查验他母亲的尸体,说不定发现过什么线索,能对他追查凶手有所帮助,却没想到祁驼子一开口便咬定他父亲是凶手。他走了回来,与祁驼子隔着一口棺材,道:“你何以认定我爹是凶手?”比起一贯的平静,他的语气加重了不少。
“床上到处都溅着血,地上也有不少血,此外还有一串沾血的鞋印,从床边一直通向窗户。”祁驼子挑起独目,“郭守业让你爹脱了鞋子,与房中那串鞋印比对,大小完全一样。你爹明明回过客房,却撒谎说没有。衣橱里的东西很乱,被翻动过,衣服都在,唯独少了一双鞋子。是你爹行凶杀人之后,因为鞋子沾了血,所以拿走了一双干净的鞋子,在外换了鞋,把带血的鞋子处理掉了。郭守业问过那些个学官,你爹在琼楼一去一回,脚上的鞋子是不是换过,那些个学官都说没注意。郭守业也问过你,你说不记得你爹早上出门穿的是哪双鞋,这事难道你忘了?忘了也不奇怪,当年你就那么点大,能记得什么。”说到这里,鼻孔里一哼。
宋慈没有忘过,凡是与母亲命案相关的事,他全都记得。当时命案发生之后,是有一个方面大耳的官员来问过他鞋子的事,然后父亲就被那官员带着差役抓走了。在父亲入狱的十多天里,他常常忍不住想,自己已经没了母亲,会不会永远也见不到父亲了?是不是自己不够细心,没留意父亲那天穿的是什么鞋子,才害得父亲被人抓走?这一想法在他脑中挥之不去,以至于宋巩出狱之后,他仍然觉得是自己的错。从那以后,他开始处处留意身边的细节,渐渐养成了无论何时何地都对四周观察入微的习惯。
“原来你是凭借这些,认定我爹是凶手。”宋慈的语气放缓,恢复了惯常的镇定,“你所说的郭守业,是当时府衙的司理参军吧?”
祁驼子没应声,只是一哼,隐隐透着不屑。
“这位郭司理,”宋慈问道,“如今身在何处?”
祁驼子把头一侧,道:“别人早就平步青云,不知高升到何处去了。”
这话似乎隐含恨意,且祁驼子不称郭守业为“郭司理”,而是直呼其名,可见其对郭守业的态度。宋慈抓住祁驼子的这一丝愤恨,故意问道:“那你为何没能平步青云,反倒沦落至此,做了十多年的义庄看守?”
“为何?你倒来问我为何?”祁驼子忽然独眼一张,“若不是为了给你爹申冤,我会沦落至此,在这义庄看守尸体?”
“原来你知道我父亲是被冤枉的。”
“知道又能怎样?”祁驼子语气里的恨意越发明显,“是你爹有冤难申,跪求于我,我于心不忍,才帮他申冤,让他得以出狱。可他呢,这么多年,他怎么不来看看我,看看如今我是什么样子?”
宋慈眉头一皱,道:“我听说,当年你查验我母亲尸体时,曾出了错。”
“我是出了错,还错得厉害!”祁驼子道,“我错在不该去验尸,郭守业明明已经验过了,我居然还跑去偷偷复验;我错在知府大人已经定了罪,我还当堂跪求复查真凶;我错在没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一个至低至贱的仵作,竟敢去高官府邸上闹腾。犯下这么多大错,活该我自受!”他抓起棺材上那几张行在会子,一把扔在地上,左手扶着棺材,右手直指大门,“走,你们一个个都走,全都走!”
这番话充斥着愤懑,响彻整个义庄。刘克庄、韩絮和辛铁柱没有挪步,都看向宋慈,等宋慈示意。
宋慈在原地站了片刻,脚下忽然动了。他不是走向大门,而是绕过棺材,走到祁驼子的面前,正对着祁驼子的直指着的手。“你既然开了口,那就把一切说清楚。”他直视着祁驼子,“为我爹申冤,难道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何必藏着掖着?”
“你这么想知道,那好,我就给你说个一清二楚!”祁驼子声音发紧,指着宋慈的那只手,慢慢地攥成了拳头。
十五年前,祁驼子的背还不算弯,有妻有女,日子安稳。彼时四十好几的他,刚刚接替师父的位置,成为临安府衙的仵作行人,跟随司理参军郭守业奔走于城内外,整日与尸体打交道。虽然做仵作很累,也常被邻里瞧不起,收入也不算高,但足够养活一家人,又因他不辞辛劳、验尸严谨,深得郭守业的器重,连知府大人都曾当面夸奖过他。
就这么做了好几个月的仵作行人,到了三月间,锦绣客舍发生了一起凶案,郭守业带领差役前去办案,祁驼子也背上装有各种验尸器具的箱子,跟着赶到了现场。现场是行香子房,一个名叫禹秋兰的妇人死在床上,其丈夫宋巩守在尸体旁痛哭,其儿子宋慈也在旁边抽泣。床上到处都是飞溅的血,床前地上也有不少血迹,还有不少沾血的鞋印,以床前的鞋印最多,不排除是宋巩发现妻子遇害后,扑到床前留下的。但还有一串鞋印,从床前延伸至窗户和窗框,极可能是凶手留下的,可见凶手行凶之后,应该是从窗户逃离了现场。除此之外,衣橱旁边还有一件丢弃在地上的衣裳,那衣裳是崭新的,布彩铺花,看其大小,应该是宋慈的。
郭守业闻到宋巩一身酒气,查问得知,宋巩中午曾去琼楼赴宴,未时将过时返回客舍,发现妻子死在了房中。郭守业又查问客舍伙计,得知禹秋兰一早外出,在未时独自返回了客房,此后没听见房中传出什么动静,直到宋巩回来发现禹秋兰遇害,客舍里的人才知道行香子房发生了凶案。
通常而言,客栈里发生凶案,无论是仇杀,还是劫杀,大都是在夜间,少有光天化日之下行凶的,毕竟客栈里白天客人进出很多,很容易被人发现。一起发生在大白天里的命案,房中还没传出什么响动,很难不让人怀疑这是熟人作案。死者禹秋兰的致命伤,位于颈部左侧,只有一粒豆子那么大,但从出血量来看,伤口应该很深,像是被某种尖锐细长的东西扎刺所致。这般形状的凶器,应该不会粗过筷子,但一定比筷子锋利得多。郭守业看着死者散开的发髻,一下子想到了发簪,问过宋巩后得知,禹秋兰有一支银簪子,是前几日宋巩在夜市上买的,禹秋兰此前用的都是木簪,对丈夫送的这支银簪子很是喜欢,这几日一直插在发髻上,但她遇害之后,发髻上的这支银簪子却不见了,郭守业命差役找遍整间客房也没能找到,可见这支银簪子极可能就是凶器,并且已被凶手带离了现场。能取得死者头上的银簪子用于行凶,再一次证明凶手极可能是熟人。禹秋兰才来临安数日,可谓人生地不熟,能称得上熟人的,恐怕只有丈夫宋巩和儿子宋慈。宋慈只有五岁,自然不可能是凶手,那么便只剩下了宋巩。
郭守业对宋巩起了疑。他查看了房中的所有鞋印,都是一般大小,于是让宋巩脱下鞋子,当场比对,可谓一模一样。他又问明宋巩在琼楼酒席间,曾在未时离开过一次,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返回。他再问宋巩有几双鞋子放在衣橱里,得到的回答是两双。可他已经查看过衣橱,里面的衣物又脏又乱,有明显翻动过的痕迹,鞋子只有一双。他派差役找来与宋巩在琼楼饮宴的几位太学学官,问了宋巩是否换鞋一事,也问了时年五岁的宋慈,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注意、不清楚。由此案情明了,宋巩有极大的杀妻之嫌,被他当场抓走,关入了司理狱。
在郭守业查问案情时,祁驼子本想现场初检禹秋兰的尸体,但郭守业说宋巩是即将参加殿试的举子,此案又发生在人来人往的客栈之中,消息势必很快传开,关系不可谓不大,所以他要亲自验尸。祁驼子知道自己成为仵作行人不久,郭守业虽然对他有所器重,但一直只让他参与一些普通命案,但凡遇到涉及高官权贵或是案情复杂的重大案子,郭守业都是亲自查办。郭守业以客栈人多眼杂为由,没有现场初检尸体,而是把尸体运回府衙长生房进行查验。
接下来的几天里,祁驼子没有接触这起命案的机会。一天夜里回家时,几个正打算外出吃酒的差役和狱卒将他一并叫了去。就在府衙附近的青梅酒肆里,几个差役和狱卒吃多了酒,聊起了宋巩杀妻的案子。狱卒说宋巩被关在狱中,受了不少酷刑,仍是不肯认罪,还不分昼夜地求着追查真凶,不管是差役还是狱卒,但凡有人进入司理狱,宋巩便会苦苦哀求,说自己是被冤枉的,没有害过妻子,又说幼子独自在外,忧其冷暖安危,求早日查明真相,放他出去。几个差役和狱卒把宋巩当成笑料在聊,笑话宋巩是个书呆子,根本就不懂怎么求人。祁驼子知道这些差役和狱卒从囚犯那里捞好处捞习惯了,在赔笑的同时,却不禁暗暗生出了一丝恻隐之心。
转过天来,祁驼子抽空去了一趟司理狱,果然如狱卒所言,宋巩一见到他便苦声哀求。宋巩记得当日郭守业赶到锦绣客舍查案时,祁驼子就跟在郭守业的身边。他对祁驼子说自己离开琼楼,是去拦住韩及其母亲讨要说法,只要找到韩及其母亲,便能证明自己所言。他又说衣橱里的两双鞋子是一新一旧,旧鞋是从家乡带来的,新鞋是不久前妻子在玲珑绸缎庄斜对面的鞋铺里买的,是专门为他殿试准备的,他还从没有穿过。当日郭守业从衣橱里翻找出来的是一双旧鞋,那么缺失的就是新鞋,依照郭守业的换鞋推想,宋巩被抓时应是穿着那双缺失的新鞋,可事实并非如此,他脚上穿的是此前几天一直穿着的旧鞋。因为妻子死得太过突然,当时他整个人都乱了,没心思去想其他,直至身陷囹圄,他才想明白了这些。
祁驼子来到司理狱,不是为了帮宋巩查证清白,只是想来提醒一下宋巩,作为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来人,要求人办事,光靠嘴是不行的。但当他看见宋巩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明明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却不言痛楚,还跪在地上苦苦求他,这番提醒便说不出口。他对宋巩实言相告,自己就是个仵作,没能力去查证这些事,一切要跟郭守业说才行。宋巩说他已经对郭守业说过了,被关进牢狱的第一天,他便什么都说了,可是郭守业不信,只是反复对他用刑,迫他认罪。
“你说过了就行,真没犯事的话,案子迟早能查清楚,大人会还你清白的。”祁驼子叹了口气,留下这句话,离开了司理狱。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很清楚,郭守业这几天很少离开府衙,可见没怎么去查证宋巩所说的事,还清白之类的话,只不过是说出来宽慰一下宋巩的心罢了。
祁驼子自知人微言轻,没能力帮到宋巩,一开始他也没打算要做些什么。只是翌日去城东办事时,从玲珑绸缎庄外路过,他却不自禁地停住了脚步。一番犹豫之后,他踏进了玲珑绸缎庄的大门,向掌柜打听了禹秋兰的事,得知禹秋兰的确一连数日来绸缎庄赶制衣服,还得知案发那天中午,禹秋兰跟着一对姐妹走了。掌柜认得那对姐妹中的韩淑,韩淑过去曾多次来选买绸缎,如今已贵为嘉王妃,居然还来光顾绸缎庄。掌柜说起此事,一想到自己的绸缎庄能得嘉王妃光顾,可谓是蓬荜生辉,就不禁眉飞色舞。祁驼子看在眼中,却是暗暗皱眉。他又去斜对面的鞋铺打听,得知禹秋兰的确曾光顾鞋铺,买走过一双男式鞋子。这一番打听下来,他知道宋巩没有说谎,郭守业的换鞋推论,可谓是错漏百出。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