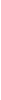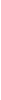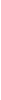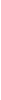卑鄙的圣人:曹操(大全集) - 卑鄙的圣人:曹操.第10部,大结局_第一章 包
新人旧人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是个邪门年头,正月伊始中原之地就被旱灾困扰着,骄阳似火,河流干涸,土地龟裂大得能伸进只手,灌溉不利庄稼枯萎,不少州郡还闹起了蝗虫。百姓苦不堪言,朝廷也想尽办法祭祀求神,直熬到六月才迎来第一场雨。哪知雨一来又收不住了,老天爷好像要把存了大半年的甘霖一口气都倾倒下来,豆大的雨点滂沱而坠,似要把大地砸出坑来。狂风卷地,时而拔树倒屋;电神雷鸣,难辨黑白昼夜。短短半个月连下九场大雨,干裂的田地被暴雨又砸又泡,没几日光景就成了黄泥汤子,低洼处积水及膝,莫说百姓田地,连朝廷屯田也没指望了。乱世征战刚理出些头绪,天灾接踵而至,万千黎庶何时才能安享太平?
七月初的一个清晨,许都城郊分外萧索。雨虽然不下了,却冷得厉害;天色灰蒙蒙,不见太阳,也瞧不清云朵,万物笼罩在一片混沌苍白的光芒中;风不甚大,但凉飕飕潮乎乎的,钻人骨头缝。本该丰收的田野如今却成了大大小小的水坑,时而落下几只寒鸦,在坑边啄着积水。远方荒原有几棵孤零零的老树,早被暴雨折磨得枝桠零落,仅剩的几片叶子在凄风中簌簌颤动,仿佛冻得打哆嗦。未出三伏竟冷成这样,实在不正常。
即便这种鬼天气,许都以东的十里驿亭还是胜友如云。锦衣绣袍香车宝马,峨冠重重揖动如云,驿道两旁挤满官员,你言我语叽叽喳喳,还源源不断有车马赶来,朝廷百官来了一大半——他们都是来给调任邺城的治书侍御史陈群、侍郎仲长统饯行的。
陈群字长文,许都人士。颍川陈氏是响当当的名门,陈群的祖父陈寔(shi)仕宦不过县令,却以清静修德、仁信笃诚著称,与同乡钟繇之父钟皓、荀彧祖父荀淑以及著名循吏韩韶并称“颍川四长”。陈寔病逝时天下衣冠之士三万余人赶来送葬,披麻戴孝者五百有余,文坛魁首蔡邕亲撰碑文,连大将军何进都派使者吊唁,传为士林佳话。陈群之父陈纪也大有贤名,董卓乱国之际险被逼着担任三公,侥幸逃亡徐州,辗转落入吕布之手;曹操水淹下邳擒杀吕布,见陈纪如逢至宝,软磨硬泡将老人家请回许都,授以大鸿胪之职,多年前也已去世。
陈群身为颍川陈氏第三代自然也颇风光,被曹操辟为掾属,又被荀彧招为女婿,仕途一帆风顺,没几年光景就担任了治书侍御史。与他岳丈荀彧相比,陈群不但拥有光鲜的家世背景,而且“通情达理”,对曹氏裂土分茅的行径,他毫无抗拒积极配合,尤其令曹操满意。在士林舆论中陈群更无可挑剔,这也得益于他的年纪,虽是陈纪之子,却比同辈人年长几岁,曾与孔融同辈论交,故而钟繇、王朗、华歆等名臣都把他当作老弟;而在荀恽、鲍勋、司马懿等一干后生眼中他又是可亲可敬的兄长。头顶名士光环,联姻高门大族,才智名声俱佳,沟通上下两代,又深谙和光同尘之道,焉能不被曹氏看重?
与陈群相较,仲长统则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出身兖州寒门,全凭读书勤学、游历四方闯出些名气,倾十余年心血写成一部《昌言》,自诩字字珠玉,却少有人拜读;曾被曹操辟为参军,但除了訾议时政少有建树,又调回朝廷任尚书郎,熬资历升为侍郎。仕途不是很顺,而且他在许都任职十年却没一个朋友,平素独来独往。
其实问题恰恰在于他引以为傲的《昌言》,仲长统分析古今历朝成败,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却大肆质疑天命、君权,抨击世家大族,甚至批判天下仕宦皆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交游趋富贵之门,畏服不接于贵尊——如此激烈言论怎能不招怨?朝中官员大多视其为异类,敬而远之。但曹操之心实难揣测,竟把他这等“穷凶极恶”之人也调去邺城,惹得许都百官既气愤又欣羡。
但嫉妒归嫉妒,送行之人还是来了不少,尤其侍郎、议郎一类的散官几乎尽数到齐。固然陈群有些名望,也不至于这么劳师动众,仲长统更不值一提,其实大伙巴结的都是魏王——无利不起早,如今的政局很清楚,魏国掌握实权,汉室朝廷就是摆设,曹氏代汉只是时间问题。在许都为官不但没前途,甚至眼前富贵都随时可能失去。所以人人削尖脑袋要往邺城钻,每逢有人调往魏廷,满朝不得志之徒都来饯行,殷殷切切,嘘寒问暖,甚至不惜溜须拍马行贿献媚,只求那人到任后向魏王美言几句,能把自己也调过去,脱胎换骨报效新朝。
今天也一样,即便雨后道路难行,车陷轮,马陷蹄,众官员还是风雨无阻百折不挠,就算弄得满身污泥形状狼狈,依旧满面春风大献谄媚——并非天下之士尽皆猥琐,只因有才识的多被网罗到魏国,有节操的不是被逼死就是隐遁了,有异志的也投奔孙、刘去了,许都自然只剩一帮庸庸碌碌、死皮赖脸的家伙。这便是末世征兆!
饮过饯行酒陈群便欲启程,无奈被众人簇拥着,碍于情面不得不搪塞。仲长统却“虱子多了不愁”,揣手望着这帮凭空冒出来的“朋友”,不住冷笑——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三俗之论岂是虚言?
二人正疲于应付,驿道上又徐徐行来两辆安车,皆驷马黑轮,列卿规制——中尉邢贞、司直韦晃两个朝廷大员竟也到了。这就不能等闲视之了,陈群忙拨开众人上前施礼:“卑职何德何等,敢劳二公相送?罪过罪过!”
司直原本只是丞相属官,负责督察京师百官、检举不法,不能与列卿相提并论。但建安九年荀彧向朝廷推荐了一位名唤杜畿的能吏,此人深受曹操器重,被任命为司直,曹操又修改官制,把司直的地位提高到与司隶校尉平起平坐,以示荣宠。但杜畿却没在这位子上坐满一年,不久就被派去接替割据河东的王邑担任太守;他到任后惩治豪强、抵抗高幹,深受黎民爱戴,使得河东郡政绩天下第一。曹操要给百官树一榜样,不忍打破他“天下第一郡守”的完美形象,故而只给他加俸禄不迁其官,竟连任了十二年。杜畿风光了,但他留下的司直之职一直空缺,最近两年才落到韦晃身上。
京兆韦氏乃一方豪族,韦晃这支却不兴旺,他本人才干更平庸,当初是因曹操经营关中的需要才被辟入幕府的,十余年间他在祭酒、令史的位置上转来转去,默默无闻低头做事,倒也安分,直至两年前雍州刺史韦康被马超攻杀,他的命运才发生转变。韦氏固然不是曹操心腹,毕竟韦端、韦康两代刺史为朝廷守边,也不能薄待;所以曹操从官场角落拎出他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摆到司直的位置上,以示对关中名门的重视。
高官厚禄从天而降,韦晃大喜过望,可赴任之后才知这是个受气的官——司直的职责是监察百官检举不法,但这些差事如今已被赵达、卢洪、刘肇等校事染指,韦晃又是老实平庸之人,不愿与他们为伍,久而久之便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做个闲人倒也罢了,问题是同僚不理解,许都官员大多把他与校事视为一类人物,表面恭敬客套,背后暗暗咒骂。没干缺德事却要陪着挨骂,这是什么滋味?更倒霉的是从邺城调至许都,官是升上去了,却脱离了魏国朝廷,前途没指望了。韦晃苦恼不已,与其当这受气的大官,还不如回邺城当小小掾吏呢。他抱定心思回邺城,但几度上书皆被曹操驳回,万般无奈也屈尊前来,想求陈群帮忙进言。
来的路上韦晃已把想说的话默默酝酿了好几遍,可这会儿真见到陈群又有些犹豫。他毕竟是二千石俸禄的高官,以列卿身份当众恳求下僚,是不是太没体面?他还在犹豫,哪知一旁车上的中尉邢贞先开了口:“长文无需客套,同殿多年情谊深厚,何必见外?”说着跳下车,三两步迎上前,紧紧拉住陈群的手——年近六旬须发斑白的老臣不惜以列卿之身讨好魏国之臣,实在叹为观止!
“邢公折杀卑职。”陈群诚惶诚恐。
邢贞攥着他手不撒开:“长文得魏王看重,担当魏国御史中丞,前途无可限量。”
“邢公过誉。御史大夫袁公近来多病,魏王调卑职充任中丞不过代理一时。卑职勉力为之犹恐不及,何敢指望高升?”其实凭陈群的名望资历到邺城必受重用,这都是客套话。
邢贞越发惺惺作态,对身边众人道:“你们听听!这才是不骄不躁谦谦君子,长文若不成一代名臣,岂有天理?”
“是是是……”全是求人来的,大伙自然顺着说。
陈群懒得再绕圈子,索性把话挑明:“邢公不必谬赞,有何驱使但言无妨。”
邢贞这才松开手,捻着胡须笑呵呵道:“何敢劳长文办事?我来不过是饯行,最近忽冷忽热时令不佳,你一路上要保重身体……”说到这儿他稍稍顿了刻,继而才道,“到邺城之后如能单独觐见,还请代我向魏王问安……”说了半天这才入正题。列卿又如何?汉家之卿不及魏国之吏,说穿了他也想另抱琵琶。
聪明人一点就透,陈群不待他说完就应承下来:“明公无需挂心,卑职一定将您这份心意转达大王。”
“多谢多谢。”邢贞喜笑颜开连连拱手。
正难以启齿的韦晃一旁瞧得分明,有邢贞示范,该怎么开口他也清楚了,终于把牙一咬,刚要起身下车,却见众官员左右闪避,揖让一位文质彬彬的青年文士走进人群——原来是陈群的内弟荀恽。
荀恽不仅是荀彧之子、陈群的内弟,更是曹操的女婿。自从曹操晋位王爵,所有女儿都被晋封公主,荀恽之妻如今是安阳公主,荀恽本人继承父亲万岁亭侯的爵位,如此身份谁敢怠慢?众官员见他都恭恭敬敬退避三舍;韦晃也不便过去搅扰,又坐下等候。
陈群素来与这位内弟关系亲厚,一见他来格外欣喜:“原以为你不来了,我还道公主治家甚严,不让你出门呢!”
荀恽只微微一笑,从怀里掏出只锦囊交与陈群:“这是小弟写给临淄侯的书信,劳烦姐夫捎去。”荀恽与其父不同,身为曹门之婿怎会反对曹氏代汉?况且他自小与曹家子侄一处玩耍,有总角之谊;尤其与临淄侯曹植志同道合,常有书信往来。
陈群刚把信收好,荀恽又凑到他耳畔,神神秘秘道:“姐丈为官多年才智出众,无需小弟杞人忧天,但眼下有桩大事格外要紧,处置不慎只恐种祸。”
“莫非魏王立储之事?”陈群早揣摩到了——如果说曹魏擅权是汉室之忧,那立储不明就是曹魏之忧。曹操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国本未定,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又会引出多少乱子?曹丕、曹植明争暗斗将近十载,至今也没个明确说法,这事已成为百官心中隐忧。可大家又敢想不敢言,连毛玠、崔琰、徐奕那等元老都因卷入争储之事纷纷落马,谁还敢公然提及?
众官员已退得很远,荀恽还是不禁压低声音:“大王立储不明,朝野之士各拥其主多有争执。大王若征询立嗣之事,您千万三思而言。”
“三思而言……”陈群凝视荀恽,细细咂摸这四字的弦外之音,似乎感觉到舅爷在跟自己玩心眼,于是顺水推舟道
:“若依贤弟之见,五官将与临淄侯谁更适合继统?”
荀恽一怔,踌躇片刻才道:“并非小弟与临淄侯相厚有意偏袒。若论德才实是临淄侯更胜一筹,文章诗赋流布天下,朝野何人不知?况坊间传言,魏王蓄废长立幼之意,前番崔琰、毛玠二公相继遇害,实因二人力保五官将所致……不过大王处事一向深不可测,即便至亲亦难忖度,传言也未必确凿。”他也不敢把弓拉满,“咱们荀、陈两家素为颍川之士影从,我父亡故,如今姐夫之荣辱不但关乎两家兴衰,也关乎门生故吏、众同乡的前程,以小弟之见还是不要弄险为妙。”荀恽声称不偏袒,却说崔、毛二老因保曹丕而死,又主张“不要弄险”,绕来绕去还是挺曹植的意思。
“嗯,有道理……”陈群嘴上这么说,心中却不以为然——荀恽并不知晓,他这位姐夫数年前就已暗中投效五官中郎将。
非但许都、邺城百官不知,连曹丕其他心腹也未必知晓,近几年陈群与其说为曹操效力,还不如说是替曹丕观望朝局,连尚书令华歆、光禄大夫董昭也在他窥伺之下,早已是曹丕不可或缺的重要帮手。按理说他与荀恽既是姻亲又是同乡,重要立场应向其坦言,不过处在当今这世道,万事都要慎之又慎。荀恽与曹植关系太好了,又娶魏王之女,就算荀恽不透露给曹植,卧帐之内对妻子说起,也非同小可。既然如此陈群索性连这个素来亲睦的小舅子也一并隐瞒,在自己妻子面前更是只字不提。
荀恽全然不知姐夫跟自己不在一条船上,还替他出谋划策:“如此最好,不过你也别怠慢五官将。倘若事不可解,我帮你周旋,毕竟我是曹门之婿。”
陈群望着懵懂的内弟,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一场储位之争从宫闱闹到朝堂,从邺城闹到许都,闹得手足同朝异心、夫妻同床异梦,真是可悲可笑!好兄弟,有朝一日你明白实情可别埋怨姐夫。我也是一番苦心,你乃曹门之婿,我又是你荀门之婿,绝不能一棵树上吊死。若曹丕为尊,陈兴荀衰,我提携你;倘曹植得立,荀兴陈衰,那时你再帮衬我。荀、陈两家攸关颍川士人之兴衰,无论如何也要屹立不倒,此中奥妙你慢慢就会懂了。不是姐夫信不过你,只是你还年轻,仕途如战场,有真刀真枪,还有冷箭暗算,倘若避匿不及中了暗箭,一人落马就能绊倒一大片。焉能不慎?
“姐夫,怎么了?”荀恽觉出他有点儿心不在焉。
“没什么。”陈群挤出一缕苦笑,目光转向远处群臣,喃喃道,“我在想……这些许都遗臣争相来送我,看似恭顺,可谁知他们心里究竟有何算计。世间最难知者——人心也!”
煽风点火
陈群、荀恽郎舅之间说体己话,来送行的群臣不便聆听,都退得甚远,各自盘算心事。已跟陈群说上话的暗暗祷告,希冀他言出必行帮忙美言;还未逮到机会的人不错眼珠盯着陈群,只待他们叙完家常再凑过去。唯独韦晃心下矛盾,刚才他已下决心开口求人,让荀恽拖了一阵又开始动摇,名声重要还是实惠重要,实在难以取舍。
就在他自己跟自己较劲之时,忽听耳畔传来一声呼唤:“这不是韦兄么,你怎也来凑热闹?”这声音韦晃再熟悉不过了,是近两年与他走动甚近的少府耿纪。
同一个地方的名门大族往往多有深交,在朝为官就会结成乡党,攻守同盟互相扶持,而且越不得志就越抱团。曹氏为政也依赖乡党,核心智囊为颍川人,地方干吏多兖州人,掌握兵马的多是沛国同乡,这三个地方的人更易得到重用,其他州郡就不免有些吃亏。关中士人势力较弱,特别是韦端、段颎那代老臣死后,许都之官唯少府耿纪、太医令吉本算得上人物,一个扶风人、一个冯翊人,却都不太得曹操信任,所以韦晃调任许都,立刻被他们拉进这小圈子;而韦晃在许都人生地不熟,有同乡照顾也觉方便,与耿、吉二人越走越近。
耿纪相貌颇为不俗,生得净面长须、目若朗星、鼻直口正、大耳朝怀,加之身材魁伟白发不多,很难想象他已年逾五旬。少府乃九卿重臣,但他今日不穿深服,不乘马车,只一身青缎便服,头戴武弁,足蹬单靴,独自骑马而来。韦晃诧异:“耿公为何如此装扮?”
耿纪捋髯而笑:“我并非给姓陈的送行,只是出来逛景。”
“旷湿之地有何景致可逛?”
“谁说无有?”耿纪举马鞭往人群一指,“这帮厚颜无耻、舐痈吮痔的官难道还称算不上奇景?”
这话正戳韦晃软肋,心头一阵狂跳:“耿公之言未免刻薄,为了功名前程又有何办法?多多体谅吧。”
耿纪却不接受这论调:“大汉乃威严之邦,以往什么时候士大夫似如今这般下作?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此皆为政者之失。”话虽未挑明,矛头却已指向曹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宦官外戚乱政已久,不能都归咎于现今世道。”韦晃毕竟是相府掾吏出身,不得不对曹氏有所回护。
耿纪并不辩驳,转而道:“韦兄官居司直,肃清风纪乃你职责,可不该来凑这热闹。”
韦晃更感羞愧,忙遮掩道:“我与长文同为相府掾属出身,总得有点儿同僚之谊吧,来送送有何打紧?”
耿纪早知他心里拨什么算盘,却故意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倒是我误会了。我还以为韦兄与邢贞那等无耻之徒同流合污,打算谄媚曹氏另谋高就呢!哈哈哈……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韦晃变颜变色:“怎、怎么可能啊!我身为司直岂会屈媚下僚?真是笑谈。”极不自然地干笑两声。
耿纪也笑了:“我想也不会。韦兄出身名门,先祖韦贤、韦玄成两代名相,忠心耿耿辅保大汉,怎会自甘堕落谄侍权臣?似你我这等家世的人可要守住良心啊!”
韦晃是名门之后,耿纪的家世更了不得。扶风耿氏乃汉室功臣,耿纪的先祖是中兴名将耿弇,跟随光武帝打天下,破铜马、讨赤眉、征张步、战隗嚣,平定四十六郡、攻克三百余城,官拜建威大将军、爵封好畤侯;兄弟子侄六人封侯,婚配皇室荣宠无比。但物极必反,至孝安帝年间,大将军耿宝与车骑将军阎显两家外戚争权,耿氏落败,族人多遭贬谪;后来又因得罪“跋扈将军”梁冀,被诛灭十余家。经这两番挫折耿氏一蹶不振,如今在朝为官的只剩耿纪与其族叔、世袭好畤侯耿援。
不过耿纪绝非如他自己所言,是忠直冥顽、谨守良心之人,为了重振家族雄风,他早年间也曾心甘情愿协助曹氏,尚书令荀彧却偏偏瞧不上他,嫌他品性阴损,共事多年始终不洽。荀彧死后耿纪窃喜,以为将有出头之日,哪知身边之人一个个调往邺城,唯独他原地踏步,身为九卿职位倒不低,却毫无实权。天长日久耿纪渐渐明白了,耿氏虽已没落终是汉室功臣,而他那位族叔耿援之妻又是孝桓帝之妹长社长公主,皇亲国戚难被曹氏接纳;况且曹魏臣僚多颍川、沛国之党,他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关中人士哪摸得到?想清楚这些,耿纪索性不抱期望了,进而对曹氏萌生恨意,只是藏而不露。而韦晃这两年虽与他来往甚密,皆属同乡之谊,并不真了解他心中所想。
他俩说话这会儿工夫,陈群、仲长统已与其他人告别,上马登程。韦晃急得直跺脚,想追过去说话,无奈耿纪一边瞧着,方才被他捧得这么高,怎好食言而肥当面出丑?耿纪早把韦晃急切神情看个满眼,嘴上却道:“该走的都走吧,省得玷污朝堂。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与韦兄甘守臣节不屈权贵,千载之后必有公论。”
他这么说韦晃更不能追了,只能坐看良机错失,不禁嗟叹一声:“唉……回去吧。”
“难得出来一趟,一同逛逛如何?”
“连日暴雨遍地泥泞,许下屯田颗粒无收,这鬼天气有何可逛?”韦晃没好气道。
耿纪手指天际道:“天人乃为一体。水旱不调,阴阳失和,此乃为臣僭越,上天示警……”
韦晃身子一颤——朝野早有议论,说天象不佳乃曹氏称王所致,曹操对此深恶痛绝,抓了不少造谣传谣之人,耿纪这种言论若传扬开可不得了,他赶紧打断:“耿公切莫声张。”
“难道不对吗?”耿纪压低了声音,口气却没变,“孝章帝章和初年大旱,乃因外戚窦宪乱政;孝桓帝元嘉年间大旱,皆因梁冀祸国所致。《五行传》有云,‘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干旱乃暴政之兆,洪涝因僭逆而起,如今两灾交替而至,曹氏是上欺君、下压民、获罪天地、人神共愤了。”
韦晃听得心惊肉跳,按理说以他的身份就该检举耿纪,但一来他品性忠厚不愿害人,再者又视耿纪为同乡挚友,故而只是苦劝:“这话万不可对外人道。”
“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天灾明摆着,难道没人说就没有了?韦兄扪心自问,觉不觉得曹氏逆天而行为恶忒多?”
无论韦晃有何倾向,曹操篡夺大权、诛除异己不择手段,这无可否认;韦晃只是低头喘着粗气,没有答复。
耿纪见他默然不语,越发放胆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臣当君尊,上下乃昏;君当臣处,上下失序。汉室社稷四百载,公道自在人心,强横悖逆之徒不得长久。获罪于天,无可祷也,人世不容,天亦不容!前几天尚书右丞潘勖暴病身亡,曹营之人皆道可惜,我却以为痛快,若非他谄媚曹氏,矫诏草拟册封魏公之文,岂能盛年暴亡?足见天不佑曹!”
韦晃无奈叹息:“是非人人皆知,然世风如此孰能奈何?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虽出身名门,自忖才智平庸,虽不求攀龙附凤,也想谋条出路,上不辱没祖宗、下对得起儿孙也就是了。”
“哼!”耿纪一声冷笑,“韦兄所言倒也有理,惜乎见识忒短。战栗戒慎,不能避祸。你以为不违拗曹操就有出路?当今曹氏所亲皆颍川之党,又以兖州之士典民政、沛国之人掌兵戎,我关中士人有何希冀?况关中诸将两度谋叛,素为曹氏所虑,若有一日改朝换代,只怕咱们都要被排挤还乡啦!”
“也不至于吧?”韦晃嘴上这么说,但联想自己从邺城调到许都坐冷板凳,不免犹疑。
二人还欲再言,忽听后方马蹄声响大作,回头望去,见一队骑兵疾驰而来。众武士盔甲鲜明气势汹汹,为首有一将官,年近五旬花白虬髯,虎背熊腰相貌威严,一边纵马驰骋一边高声喊嚷。在许都无人不识此公,乃相府长史王必——他早年随曹操起家,披荆斩棘广有功勋。十二年前曹氏移居邺城,建立冀州府,后又改造为魏廷,许都的丞相府便只剩空壳。曹操恐再有昔日“玉带诏”之事,任命王必为留府长史,明为处理杂务,实是统领一支兵马威慑百官,应对不测。
韦晃刚说了两句犯忌讳的话,正心中不安,一见王必驰骋而来,以为是来
抓自己的,险些跌落马车。哪知王必转瞬即到,却从他车边一闪而过,口中大呼:“长文、公理!慢行一步,愚兄来送你们啦!”原来也是饯行的。
这才是无所图谋、真凭交情来送别的,陈群、仲长统听到呼唤立刻拨马回迎,三骑凑在一处有说有笑。韦晃松了口气,耿纪却又在他耳边嘀咕道:“你瞧瞧,他们才是一路人。姓王的是曹氏爪牙,陈群乃颍川乡党,仲长统再没人缘也是兖州山阳郡出身,如今就他们这帮人得志。你不违拗人家,可人家自有心腹,哪把你当自己人?”
韦晃胸中郁闷,竟觉得这话有道理,却见王必身边除了士兵还有个三十出头的皂衣士人,身躯矫健相貌英俊,甚是眼熟,却又想不起:“王必身边那年轻人是谁?”
“韦兄贵人多忘,那是咱关中同乡子弟,已故武陵太守金旋之子,议郎金祎金德伟。”
“哦。”韦晃想起来了,他常去太医令吉本府上做客,金祎却与吉本的两个儿子吉邈、吉穆是好友,曾经见过一面,但年龄地位颇为悬殊,没说什么话。
耿纪撇嘴摇头:“这小子也算好样的,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而且极善骑射,惜乎处世糊涂,整日与王必厮混。”
说来甚是可叹,金氏也是京兆名门,乃孝武帝托孤重臣金日磾(mi di)之后。金祎的伯父金尚品行高洁,与同郡韦端、第五巡并誉为“三休”(金尚,字元休;韦端,字休甫;第五巡,字文休,东汉名臣第五伦之后)。当年曹操举兵,靠袁绍矫诏成为兖州刺史,而西京朝廷任命的真正刺史就是金尚。曹操不肯让权,便派兵把金尚逐出兖州,辗转流落袁术帐下;袁术僭越称帝,金尚拒不担任伪职,终于遇害。后来曹操奉迎天子重建汉都,对当初之事颇感遗憾,提拔金尚之弟金旋,也就是金祎的父亲。建安十三年征讨荆州刘琮投降,曹操委任金旋为武陵太守,想要予以重用;哪料赤壁战败江南不保,刘备争夺四郡,金旋兵败丧身疆场。曹操本想补金家个人情,不想又害一条性命,无可奈何又让金祎入仕,任命为郎官。只是金祎年纪尚轻,留于许都未及升迁;王必了解内情,又欣赏金祎武艺出众,便时常带在身边,与他谈文论武,天长日久竟结成了忘年交。
韦晃遥望满面笑靥的金祎,甚感失落:“人家年纪轻轻却比咱这帮老家伙吃得开,惭愧啊……”
“惭愧什么?他的前程是靠父辈两条性命换的,我都替他害臊!”耿纪拍着自己脸颊,“他若真明理,就该与曹家为仇作对。”
韦晃不禁蹙眉:“何必计较以往,年轻人以前程为上。再说曹金两家之事乃天意造就,也谈不上仇怨。”
“人活一世争口气,况乎身有才智岂能荒废?金祎若有气节就当自谋前程,即便依仗别人也不能靠曹氏。我也是一片好心,怕这孩子少不更事,受世人唾骂。”
跟着曹家就受世人耻笑?韦晃越发不安:“耿兄说话一定小心,你我之间也罢了,这话传扬出去祸及满门哪!”
“有何可惧?我还有好多心里话没说呢。”耿纪四顾,见送行的官员都已离去,便跃上韦晃马车,凑到他耳边,“曹氏阉竖之后为臣不正,我关中雄杰焉能辅保此家?实言相告,我早有反曹之意,惜乎未逢其时。”
“啊!”韦晃惊得呆若木鸡。
“怕什么?”耿纪攥住他手腕,“新人笑旧人哭,一朝天子一朝臣。倘若败亡不过一死,曹氏称帝又能给咱什么好处?与其庸庸碌碌,不如放手一搏。我早就设想过,曹氏惺惺作态自称汉室之臣,若扶持天子登高一呼,必能撼动九州瓦解贼党。韦兄虽非曹氏一伙,毕竟是丞相司直,曹操千防万防也防不到你身上,正好遮人耳目居中联络;吉本掌管御医出入宫禁,临事之际控制天子亦非不能;金祎深得王必信任,倘能把他也拉进来,除王必易如反掌,许都不就在咱掌握了?那时诏告天下讨伐曹氏,必能……”
“我不听,我不听!”韦晃挣开他手,哆哆嗦嗦捂住耳朵。
“你已经听见了。”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没听见。”韦晃战战兢兢,瞪着恐惧的眼睛,却不敢再看耿纪。
耿纪见他这般失态,唯恐招人起疑,忙跨回自己马上,嘴里嘀咕着:“大丈夫快意恩仇,岂可怯懦畏缩?”
“我不干……我不干……”韦晃不住颤抖着。
耿纪眼珠一转,反倒笑了:“都说你韦晃乃一无用之人,想巴结曹操都巴结不上,我原先不信,今日才知不假。也罢,反正肺腑之言都对你说了,你不妨向曹贼告发我,说不定还能换来富贵呢!只盼你日后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荣归故里时好好向关中父老夸夸口,说说你是如何出卖同乡博取功名的!”
再窝囊的人也有三分气概,这话韦晃听来如刀子扎心,摆手道:“你也忒小觑韦某了。罢罢罢,你要如何我一概不问,只莫对我言。”
耿纪暗甩一把冷汗,但要掩曹氏耳目必须有韦晃参与,无论如何都要拉他下水:“痴人,目光放远些。曹贼年迈久不立储,其实危险得紧。去年远征汉中半途而废,空留夏侯渊一莽夫坐守;前不久张郃又被张飞击退,长此以往汉中焉能保全?况马超已投蜀中,此人素得雍凉羌氐之心。咱只要抓准时机控制许都,传檄关中豪杰一并举兵,那时刘备兴师汉中,马超招旧部于西凉,加上羌氐群起响应,关西之地立时非曹氏所有。青徐沿海臧霸、孙观等将拥城自治,本非曹营嫡系,西南诸郡蒯祺、申耽之辈也未尝甘于顺服。再说江东还有孙权,众志成城何愁曹贼不败?”说到这儿耿纪手托须髯,闪过一丝得意之色,“莫看你我现在无权,那时不一样了。进可征讨河北诛灭曹氏,退可迁都长安保守乡土;成可执掌朝纲号令天下,败亦可将天子转献刘备,不失功勋封侯之位。这并非险途,乃是康庄大道,韦兄不动心吗?”耿纪这番算计不可谓不深,分析时局不可谓不精,但也暴露了真实嘴脸——曹操欺君篡国固然有悖纲常,耿纪又何尝是善类?方才那些君臣大义的话都是虚言,他反曹其实是出于仇恨和野心!
“不、不……”也不知韦晃听进去没有,只一个劲摆手。
耿纪还欲再言,却见王必已带着金祎转回,忙嘱咐道:“我突然告知,你心中难免恐惧,没关系,你回去想想,咱改日再谈……”说话至此王必已不甚远,耿纪倏然变作笑脸,提高嗓门拱手道,“王长史,一向未会别来无恙?”
王必虽与耿纪无甚话说,但面子上总需过得去,抱拳还礼:“耿公客套了。”
耿纪故作关切之态:“长史方才带的兵呢?怎只剩这四五人?”
“我派给陈群二十小卒,护卫他们以防不测。”
“长史真是热心人。不过您肩负国都安危,倘有不逞之徒行刺可非小事,您身边得多带兵啊!”
王必回头一指金祎,笑道:“有德伟在旁,料也无妨。”
“最近时气不佳,王长史身体可好?”耿纪指了指呆坐的韦晃,“韦公这会儿就有些不适。”
王必兵胁百官自非粗疏之人,早察觉韦晃神色不正,听耿纪一说信以为真:“难怪脸色苍白,受寒了吧?”
韦晃心内慌张,强挣着点点头。耿纪岂容他说一个字,忙插话:“最近时令不佳多人染病,前日潘右丞病逝,今日韦公又受风寒,王长史也要注意身体,魏王还依仗您呢。”他说这话时诚惶诚恐,真似发自内心一般。
“蒙您关照。”王必还挺领情,“野外阴湿二位不宜久留,在下还有差事,先行一步。”说罢回头招呼亲兵。
“送大人。”耿纪又施一礼,却瞟向金祎,挤眉弄眼轻轻招手。
别人招呼金祎未必肯应,但耿纪是同乡长辈,焉能不理?向王必请示:“既然韦公不适,我留下照顾他老人家回府吧。”
王必也没在意,只点点头,带兵先走了。金祎这才询问:“耿公有何赐教?”
“唉!”耿纪未开言先叹气,“你这年轻人,叫我说什么好呢?方才许多人背后议论你,说你……说你……唉,不提也罢。”
金祎年轻气盛,怎受得了这一套?忙追问:“他们说我什么?耿公但言无妨。”
耿纪故意吊他胃口:“是非只因多开口,还是不提为妙。”
背后议论必非良言,金祎急得摩拳擦掌:“您倒是说啊!咱都是关中之人,若从先父那里论起,我还需叫您一声叔父,有什么话不能对小侄明言?”
耿纪紧紧蹙眉,好似下了多大决心一般,良久才道:“有人说你不忠不孝认贼作父啊!”
“可恼!”金祎焉能不怒,“何人如此辱我?我宰了他!”
“你看你看,不愿告诉你,就怕你毛毛躁躁。说这话的人多了,你杀得完吗?身正不怕影子歪,踏踏实实走自己的路。”
“忒气人啦!”金祎眼睛都瞪圆了,拳头攥得咯咯直响。
“傻小子,世上烂人太多,与他们生气不值得。”耿纪抚着金祎背膀,“你这孩子有出息,依我说比曹家荀家诸子都强,惜乎就是少点儿城府,虑事不周全。”
金祎拍着胸口声嘶力竭道:“小侄自问生平无愧,焉能被无耻之徒这般诋毁?决不能善罢甘休!”
耿纪连连摇头:“你既认我这个叔父,我可得教训你两句。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既然有人议论你,必是你尚有不当之处。想来昔日你伯父受任兖州刺史,若非被魏王驱逐怎会死于袁术之手?你父若不是被魏王派去江南,何至于遭刘备屠害?固然这都是机缘造就的,但常言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你如今与王必关系这么近,难免遭人诟病……”
伯父、父亲之死金祎当然不会忘,但那些事不是曹操有意为之,况且他在王必照顾下仕途顺利,想到前途光明,陈年旧怨就抛开了。但今日被耿纪这么一挑,金祎心头那块伤疤又揭开了,尤其那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更是振聋发聩,激得他五内俱焚。
耿纪脸上绽出一缕微笑,越发软语温存:“你还年轻,切忌意气用事,谁是帮你的,谁是害你的,一定要分清。官场险恶人心难测,以后遇到难处只管来找我,老夫虽无权,毕竟为官三十载,给年轻人指指路还不成问题的。唉!可叹你伯父、父亲不幸早亡,留下你无依无靠怪可怜的。”
金祎望着耿纪慈祥悲悯的眼神,心里热乎乎的:“多谢叔父照顾。”说罢低头暗忖——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堂堂男儿不可负恶名于天下!
耿纪见他如此神情心头暗喜,又重重地拍了拍他肩膀,嘱咐道:“年轻人不可忘本,名声很重要,千万不要忘记曹孟德对你金氏一门所作所为啊!”
“当然不会。”金祎被他激得满面绯红、咬牙切齿,半晌才稳住心神,抬头再望,耿纪已拨马而去;只剩韦晃颓然呆坐,脸色苍白、二目空洞,不知想些什么……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