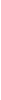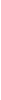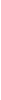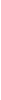七杀简史 - 音乐小子杀戮(1991年3月22日)_一
一
——你觉得他在打瞌睡吗?
——老大,咱答不上来。
——什么?唉,好吧,把他的牢房指给我看。
——两分钟前我就指过了。地牢里似乎根本没有别人。
——地牢?这么说好像不太合适吧。
——你结束了自己出来。
——你不一路陪着我?
——不喜欢黑暗。
我的脚步声在回荡,我唯一的念头就是真希望我能看见自己。不是开玩笑。他们太他妈喜欢狗逼贱货格里塞尔达·布兰科的风格了。一个邪恶的点子,在牙买加发扬光大。不得不夸奖一句那个销声匿迹的臭婊子,撇去别的功劳不提,她至少留给我们一个了不起的发明。事情是这样的。老爹乔西正在数日子,等待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罪名有谋杀、勒索、妨碍司法、贩毒,等等等等;现在说了算的是他儿子本吉·威尔斯,小伙子已经长大了(但比他老爸更胖、更黑、更一脸厌倦),以唐的身份统治哥本哈根城。更像是摄政王或代理人之类的角色。于是本吉组织起了罗爸爸纪念杯年度板球大赛。总而言之,也就是在西金斯敦东头的国王街召开会议。西金斯敦的唐去东边已经够让人头疼了,他孤身一人骑着摩托车出发则是雪上加霜。他来到路口,眼望前方,脑子里想自己的事情,而另一辆摩托车在他旁边停下。等他扭头去看是谁的时候,两个黑衣人已经开火,把他的心脏打得从胸口飞了出去。
有意思吧?本吉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老爸是乔西·他妈的威尔斯,他从小到大都看人开枪,他周游世界——好吧,美国——去高级学校,一辈子没有哪一天是饿着肚子上床睡觉的。你还不明白吗?一个他妈的枪手,却过惯了好日子。他和中央公园西路爹妈公寓里随便走出来的一个小毛孩没有任何区别。他父亲至少让这个国家三次陷入僵局,此刻待在监狱里总算要从天上跌回地下了,咱们的金童干了什么?他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出门了?他到底在想什么,觉得其他的枪手都在教堂里?一次格里塞尔达风格的暗杀不可能来自狗屎运。他的死不仅是个陷阱,而且安排得异常妥当,甚至详细到了具体的十字路口。那些年轻人,他们根本不动脑子。我他妈老了。我曾经觉得“老”就是你弯下腰再站起来的时候会啊地痛呼一声。现在我觉得“老”是遇见敌人却觉得我老得没法战斗了,以前的战斗留给你的只有怀旧情绪,而怀旧情绪只能用来下酒,而不是拿来开枪杀人。
头部和胸部的射入伤,头部、颈部、肩膀和后背的射出伤。上周我和那天早晨主持急诊室的洛佩斯医生谈过。他妈的血逼,他说,我这辈子都没这么害怕过。不是对个人安危的简单恐惧,而是害怕末日会降临在急诊室。本吉·威尔斯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死透了,医生能做的只是宣布死亡。但护送本吉而来的是三千名气势汹汹的暴徒,围得急诊室里里外外水泄不通。医生能做的只有记录死亡时间,但三千个人围着你,指望你化身耶稣,因为医生就该为唐这么做,这时候你将体验到最荒诞的一场戏,可惜这场戏不叫歌舞伎。洛佩斯医生向我一五一十讲述这些。他们必须把本吉转移到病床上,虽说这已经是在浪费空间了,但当时人群在高喊“救活本吉”,声音响得一英里外的山谷里都能听见。他们首先尝试打通气管,急救的第一步永远是这个,目的是控制住灾难性的大出血。可是本吉被送进医院的时候,他的肺里已经
只有血液了。外面的人群越喊越响,医生不得不在一具尸体身上演他妈的戏。你想象一下该怎么让血液已经停止循环的尸体恢复血液循环。没有脉搏,没有血压,没有任何程度的意识。不是说他暂时失去意识了,而是他已经他妈的玩完了。我问医生打算什么时候告诉群众他已经死了,他说,不骗你,老大,从我们开始抢救他的那一刻起,我也在期待奇迹。外面的人群推搡得太凶,挤破了两扇玻璃窗。
做心脏电除颤是最可怕的。他们每电击本吉一下,尸体就抽搐一下,整个人群也随之跳动一下,连外面根本看不见里面的人也一样。电除颤,尸体抽搐,人群跳动。电除颤,尸体抽搐,人群跳动。电除颤,尸体抽搐,人群跳动。过了一个小时,洛佩斯医生终于宣布了一小时前尸体被推进来时就该宣布的事实。然后,哇啊!医生没救活他的消息在人群中流传。本吉·威尔斯死了。他们首先踹倒急诊室的大门。三千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大多数带着枪,剩下的都是能空手裂虎豹的那种角色。我们操你妈的大血逼。我们要宰了你妈所有人,我们要屠平整个血逼的医院。五十个医生护士换本吉一条命。几个男人抓住一个护士扇她耳光。洛佩斯医生说他扑上去阻止,但两个男人抓住他,用枪托砸他脑袋。他们掀翻接诊台,可怜的保安做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逃跑。医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发生的,但很快就有新一波浪潮席卷了人群,他们高喊杀死本吉的不是医生,而是民族党。
星期天夜里,他们袭击了八条巷的六号巷。他们见到男人就开枪,碰到女人就强奸,焚毁三分之一房屋,打死了几个孩子表达决心。两天后,他们荡平了三号巷。接下来,他们将战火烧到迈阿密,驾车放冷枪,在本田雅阁和俱乐部窗户上留下弹孔。我的两个哥们儿说牙买加人在劳力士俱乐部里展开枪战,他们险些没逃出来。总理不得不联系劳动党以谈判停战,不得不请教会出面组织和平游行。只有在杀戮扰乱了本吉的葬礼安排时,他们才暂时罢手。我没有参加葬礼。事实上我绝对不能出现在那儿。好吧,我撒谎了。我确实去参加了葬礼,但估计他们误以为我是保镖或其他什么人。上次见到这么盛大的葬礼还是送别歌手的时候。
至少两万人。前总理当然也在。不用说,1976年他是反对派,1980年当上总理,1991年又回去当反对派了。首先出场的是仪仗乐队,差不多就是新奥尔良的阵势,男人身穿雪白的制服,姑娘穿带小绒球的红色迷你裙。然后是灵柩,黑色实木,银质把手,死去的小子身穿黑色天鹅绒正装。既然你再也不会出汗了,穿冬季行头出殡有什么不好?他妈的白马拉着玻璃灵车,载着灵柩紧跟仪仗乐队出场。接下来是前总理与本吉的正宫婆娘,女人穿紧身小黑裙,粗大的金项链就是饶舌弟兄们戴的那一种。还戴着特大号耳环的女人。你看见她,就会注意到在场的其他女人。金丝锦缎迷你裙,粉色迷你裙,白色迷你裙,渔网袜,银色高跟鞋,鸟形帽子,帽子如鸟,更多的金项链。有个姑娘穿大开叉的黑色礼服裙,往下一直露出了臀沟。这么多女人走在街上,就仿佛那是时装表演。
乔西申请出狱(这么说真是挺奇怪的),去参加儿子的葬礼,但当局不允许。他们为什么会允许?放一个唐离开监狱,投入两万名拥护者的怀抱,你说他们还怎么让他回监狱?美国政府大概听说了这个消息,高喊了一万声不行和没门。真是有意思,整个八十年代乔西都在建立
他的帝国(当然是在某些人的鼎力支持下),他们却对他不屑一顾。他妈的纽约啊,哥们儿,我对他说过他不该做那件事。黑小子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1985年的那一天,乔西·威尔斯从无名小卒一步登天,爬到缉毒局和联邦调查局要犯名单接近榜首的位置。劳动党失势之后,他立刻变成了他妈的活靶子。
但祸根早就埋下了,生意做得越大,他就越是嚣张。有一天乔西在路上开车——我不记得具体是哪条路了,总之是在一个叫德纳姆镇的地方。乔西径直撞上一辆公共汽车。他跳下车,大发雷霆。但司机一时间也气得发疯,抽出一根撬棍。天晓得他说了什么,反正他上蹿下跳,大喊大叫威胁要怎样怎样。有个女人大喊“那是乔西·威尔斯”,整条街顿时清空了,只剩下可怜的公共汽车司机,这会儿他倒是闭嘴了。他像飞奔鸵鸟似的跑向警察局,乔西甚至都懒得看他。可怜的家伙。三十分钟后,乔西·威尔斯带着十个弟兄走进警察局。他们大摇大摆走进去,抓住司机,又大摇大摆走出去。没有一个警察敢站起来。那家伙吓得拉了裤子,看见警察在自己的警察局里纷纷转开视线,他哭得像个女学生。那帮人就在警察和其他人的注视下当街干掉了司机,有枪的开枪打他,没枪的拿刀捅他。就好像乌鸦扑向刚死的猎物。警察当然逮捕了乔西,但检察官找不到证人。一个也没有。
另一方面,卡利集团说这个狗娘养的够他妈狠,没有哪个狠人比他更他妈凶。把英国给他和他的匪帮。
他带着手下去雷马,光天化日之下杀了十二个人。为什么?因为雷马有人抱怨说他们的小社区不受重视。乔西喜欢清清楚楚地亮明态度。警察发出通缉令,乔西逃往美国,他在美国变成涉案关键人,又潜逃回牙买加。警察送他上法庭,但唯一的证人突然得了失忆症——哦,不,等一等,她其实不在场——哦,不,等一等,她有很久没去验光换眼镜了,所以她瞎得像只蝙蝠。说真的,她不记得了,整件事就是一团糨糊,因为当时枪声大作,子弹乱飞。
但就在去年,他女人和男朋友走出某家夜总会,八条巷的歹徒不知从哪儿钻出来,朝两人开火。他们把男朋友打成了瑞士奶酪,直到找不到地方继续镶子弹为止。姑娘蜷缩成一团,他们走到她身边,干净利落地爆了她的头。我心想他们至少没有先奸后杀。我一直不确定他们知不知道她究竟是谁。我的意思是说,就好像迈阿密的格里塞尔达,你对敌人步步紧逼,他们迟早会有反击的一天。假如你不停树敌,敌人就迟早会超过临界质量。你制造出比你更无情的敌人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毕竟是你在不停升高标杆。咱?咱从来不在同一个地方待太久,免得惹出一群敌人。这东西和其他关系一样,也是慢慢培养出来的。这也是我不为哥伦比亚或金斯敦卖命的原因。我是一名服务商。说到临界质量,联邦调查局对乔西提起了多项指控,他们很想抓他归案。贩毒大战肯定会有赢家,但绝对不会是个凑巧撞了大运的加勒比屁眼岛黑鬼。这次他们要他进监狱,这次他们要他烂死在监狱里。
对,我去监狱找过他,而且不是在探视时间内。我说嘿乔西,他立刻在床上坐起来,花了好一会儿端详我。等他看清楚了,他露出微笑,但笑容很浅,就好像他有点害羞。然后他说:
——我知道他们会派你来。
——过得怎么样,我的孩子?
——显然你过得比我好,大爱医生。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